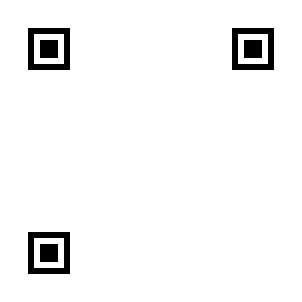事情还是马上解决的好,再拖下去可能会成为另一桩悬案。
韦方突然想到穗穗娘——她现在怎么样了?没人看她,她的饮食起居是不是有困难?杨局长让他放宽心:“王龙那小子,安排了一个老实的外地人去给她送饭,他哄道‘你是新来的,她不认识你,她怕你哩,不敢给你放蛊的。’小伙子还真信了!这几天都是他给穗穗娘送饭的。哈哈,王龙真精,亏他想的办法!”
韦方问:“那小子没事吧?”
杨局长说:“没事没事!活蹦乱跳的!王龙说了,等几天出来大太阳,让道师选个日子去晒草蛊。”
“是么?”韦方不知道说什么,他突然很可怜穗穗娘,隔着玻璃,韦方小心翼翼偷看着那传说中的草蛊婆,曾经杂乱无章的头发已被细致的挽上,因为很久没洗,油光鉴亮,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顾自发呆。韦方很想冲进去,将所有的疑问全盘托出:那银锁是不是她委托老板铸的,里面有什么秘密?为什么对县里的那朵多人下药?她又是怎么练蛊
当然,他还没有这样的胆量,所有的话都凝住了,只在门口徘徊了一阵子,便怏怏地离去了。
林卉的遗体,随着丈夫,一同迁往寨子的祖坟。韦方也跑去帮忙了——他还想顺便去拜会一下已经被传的神乎其神的张道师。从他那里也许能得到接近穗穗娘的办法。
当他再次见到张道师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土里土气的农民就是县城里威风凛凛的张田富道师。听说县里有人来看他了,张田富可是抛了地里的活,趾高气昂的跑来了,但是,来人似乎没有什么诚意,像看猴子一般打量着他,然后哼哼哧哧说了:“我是来请教预防蛊毒的办法的。”
预防?呵呵,新鲜词!张田富很乐意同这类“新鲜人”打交道,然后他换上刚学的新鲜词——就成了他炫耀的资本,他很快就明白了“预防”的意思,然后现学现用,跟韦方说道:“每个下药的,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练药术,防得了这个防不了那个,怎么预防?只能对症下药!”
韦方问:“你能破解同一个蛊婆下的蛊吗?”
张田富没听懂,韦方说:“大伟他娘还在拘留室了,现在没人敢接近他,案子也搁在那里停滞不前。”
张田富眯起眼睛,像是在搜索回忆:“向大伟?哦,我知道的,他本来可以不死的。”
韦方补充道:“放蛊的,就是他娘。”
张田福说:“我晓得。”
韦方说:“那是他亲生儿子,他都没有放过!”
张田富一本正经的说:“谁知道呢?蛊婆不把蛊放出来,她自己就会出事。哎!可怜呐!”
韦方问:“有没有什么接近她的办法?”
张田富煞有介事地说:“我见过那个女人,她的道行还不是很高,如果她要作祟,会把药下在食物里,你要记得,她给你的东西千万不要吃,也不要在她百步之内吃东西。”
韦方应诺。